葛剑雄:童年生活中的江南“粪土”
- 大数据
- 2025-04-13 10:32:04
- 18
李伯重教授《粪土与历代王朝兴衰的关系》一文中有关江南“粪土”的叙述勾起了我对童年生活的回忆,也可印证伯重兄所引的史料。
1945年我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(今属湖州市南浔区)宝善街,1956年夏迁居上海。因我幼时记忆力颇强,加上一个衰落中的市镇没有什么宏大题材,日常生活反能留下较深印象。

南浔古镇
从近年发现的《南浔研究》(当时小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形成的社会调查资料)原稿得知,20世纪30年代镇上已有几处公共厕所,但到50年代初每家每户还都使用马桶,倒马桶便成了家庭主妇或女佣的日常家务。不过,家里的女人不必亲自倒马桶,至多只要将马桶拎到家门口,因为每家的马桶早已由惜粪如金的农户承包了。每天清晨,都会由固定的农妇或她家的大女孩将马桶拎去,倒入她家的粪桶后再洗刷干净,送回原处。如果主人不介意,也可不必将马桶拎出,由农妇直接到房间取。但送回时都送在门口,还将盖子斜放,开着一半,一则告诉主人马桶已倒过,一则便于风吹干洗刷时弄湿的马桶沿,免得主人使用时不舒服。到80年代我第一次在广东的餐馆用餐,见友人将茶壶盖打开一半斜放在壶上,得知这是提醒服务员添水,不禁想起那时家门口斜放着盖子的马桶,差一点笑出声来。
也有讲究的主妇嫌乡下人洗得不干净,会自己拎到河边,用专用的马桶刷子再刷洗一遍。这种刷子一尺多长,用竹子劈成细条扎成,南浔方言称之为“马桶甩(音hua)洗”。如果主妇抱怨,农妇会忙不迭地赔不是,保证第二天一定洗刷得更干净,因为怕失去一个粪源。我家自然也备有马桶甩洗,但母亲用的次数不多。南浔人在指责别人或自己孩子满口脏话时,会骂一句重话:“嘴巴要拿马桶甩洗刷刷了。”
对农家来说,粪源就是肥源、财源,特别是承包马桶,更是固定的日常粪源,必须确保。按惯例,四时八节,农户都要给马桶主人家送时鲜蔬菜和自制食品,过年前送得更多,一般有新米、糯米、鸡蛋、鸡、肉等。农户自给自足,送的东西都是自己种的或自家地上长的,如有的农家有片竹子,就会送春笋、冬笋;有的农民会捕鱼抓虾,就送鱼虾。自制食品一般会有熏豆(毛豆煮熟后用炭火烘干)、风消(糯米饭摊在烧热的铁锅上用铲子压成薄片烘干)、年糕、粽子、炒米粉等。礼物的多寡虽与农户的能力及双方的亲疏程度有关,但主要还取决于粪源的数量和质量,人口多的人家不止一个马桶,量大;成年男性多,马桶中粪的含量高。以承包马桶为基础,双方往往会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。农户为巩固粪源,防止他人争夺,会尽力讨好主人。主人也会有求于农户,如家里有婚丧喜事要采购食品,到乡下上坟时有个歇脚地,孩子要雇奶妈或寄养,临时找个佣人或短工,出门搭个航船,都得找熟悉的乡下人帮忙。而来家倒马桶的人天天见面,联系方便,又信得过,往往认了干亲,相互以“干娘”“过房女儿”相称,结成比一般亲戚还密切的关系。
当地习俗,男人除了使用外不能接触马桶,否则于本人与家庭都不吉利,拎马桶、倒马桶、洗马桶都是双方女人的事。承包马桶的农户一般离镇不远,都用粪桶将收集到的粪便挑回去,集中在自家的粪缸中。大多是由女人将空粪桶挑到承包户附近较隐蔽处,倒完马桶后由家里男人来将粪担挑走,也有女人自己挑回去的。有的农户承包的马桶多,或者路远,会搭航船回家,将装满粪便的粪桶挑到船上,放在后梢。为了不招致镇上人讨厌,倒马桶的人一般都起得很早,挑粪的人也尽量走偏僻的小路或弄堂。偶然见到直接将粪便装在船舱里的粪船,那是运公共厕所或学校等单位里厕所的,当然也需要预先订购。
不过到我离开南浔的前一二年,镇上有了“清管所”(清洁管理所的简称),并且出现了由清管所工人推着的统一式样的粪车,上门倒马桶的农妇消失了,居民自己将马桶倒入粪车或新建的公共厕所内。我父母在1954年就去上海谋生,我们姐弟虽还住在家里,却是由外婆来照
料的,我已记不得来我家倒马桶的人什么时候开始不来了。现在想来,这大概是农业合作化的结果,粪源归集体了,农户自然不能再个别承包倒马桶。种田开始用“肥田粉”(化肥),粪肥独秀的格局改变了。

马桶
1956年我也到了上海,随父母住在闸北棚户区的一处小阁楼里。每天早上都会听到马桶车轧过弹硌路的声音,大弄堂里会传来“马桶拎出来”的喊声,母亲会随着邻居将马桶拎到粪车倒掉,然后在给水站(公用自来水龙头)旁洗刷马桶。有人在马桶中放一些毛蚶壳以便刷得更干净,于是传来特别响亮的刷马桶声。1957年我家搬到共和新路141弄,住在弄堂底,马桶车进不来,后来建的倒粪便站也在弄堂口,加上母亲早上要上班,只能将倒马桶包给一位大家称为“大舅妈”的中年妇女,每月付费1元。一次母亲与南浔的亲戚谈及,他们觉得不可思议,家里的马桶给她倒,非但得不到好处,还要倒贴钱,“难道收粪的不给她好处?上海人真门槛精!”
在南浔时,亲友和同学中没有大户人家,住房都不大,大多没有“马桶间”,马桶就放在卧室一角或蚊帐后面。我们从小被教的规矩是,到别人家里去时不要喝茶,尽量不要用马桶,特别是女孩子。只有过年可以例外,因为南浔过年待客时要上甜茶(放风消和糖)、咸茶(放熏豆、丁香萝卜干和芝麻),不喝是失礼的。有时小孩喝不完,大人会帮他喝光。但到乡下去就没有这样的限制,因为农家都欢迎使用家里的马桶,送肥上门。不用说亲友上门,就是路过的陌生人,无论男女老幼,只要说是“借你家解个手”,或“急煞了”,马上会延至马桶前。有的农妇还会热情介绍:“这只马桶刚刚刷得清清爽爽”“汰手水搭你放好了”。
草纸当然会放在马桶旁。如果主人家正好有空,还会泡上茶留来客休息一会儿。如来客喝了茶,又及时转化为小便,那就上上大吉,一定会更热情招待。就是家中没有人,只要门没有关上,过路人也可以堂而皇之进屋使用马桶,主人回来绝不会怪罪。
为了广开粪源,乡村的路旁不时可见掩埋着的大粪缸,缸口高于地面,缸缘铺上一块木板,供过路人蹲在上面方便。有的还在上面盖上简易的稻草顶,为使用者遮阳挡雨;木板前方横一根竹木把手,以减轻使用者久蹲的疲劳,并便于结束后起立。但这类简易厕所总不会全部封闭,大多全无遮挡,使用者在内急时也顾不得那么多,所以我们在乡间行走时,不时从后面看到蹲客的半个屁股,或者见到撅起的屁股正在完成最后动作,早已见怪不怪。我们男孩小便时自然不愿站到粪缸上闻臭,随便在路边田头找个地方。要是给农妇看见,一定立即制止,并热情邀请:“小把戏,乖,到这里来撒!”或者说:“我这里有豆,撒好后拿一把吃吃。”如果有自己的孩子与我们在一起,必定招来怒骂:“个青头硬鬼(音举),笨得勿转弯,还勿快点叫两个小把戏撒在自己田里!”
路旁随处可见的大粪缸固然是农家上好肥源,可换来满仓粮食,但也给路人与乡村本身带来很大麻烦。一是臭气熏天,因为粪缸都是敞开的,最多在上面盖一层稻草。特别是夏天,在骄阳下,粪缸中水分与臭气一起蒸腾,掩鼻而过也受不了。二是不安全,走夜路的人不小心跌入粪缸的事时有所闻。暴雨后粪水横流,农民在河里洗粪桶,造成河水污染,而农民为节省柴草,夏天一般都喝生水,用冷水淘饭。粪缸上苍蝇成堆,农民家中也满桌满灶。造成传染病流传,又得不到及时防治,常有农民不明不白“生瘟病”死掉。幼时常看到一群人抬着病人从乡下赶往医院,有时跟着去看热闹,不久就听到哭声震天,抬出来的已是一具尸体。
到上海后常在暑假回南浔,再到乡下走走,见露天粪缸逐渐消失,代之以公共厕所。镇上居民用上了自来水,有了集中处理粪便的水冲厕所,已有人家用抽水马桶。尽管镇上人家的马桶还沿用了很久,但农户承包倒马桶从此成为历史陈迹,只有我们这一代人还保留在记忆之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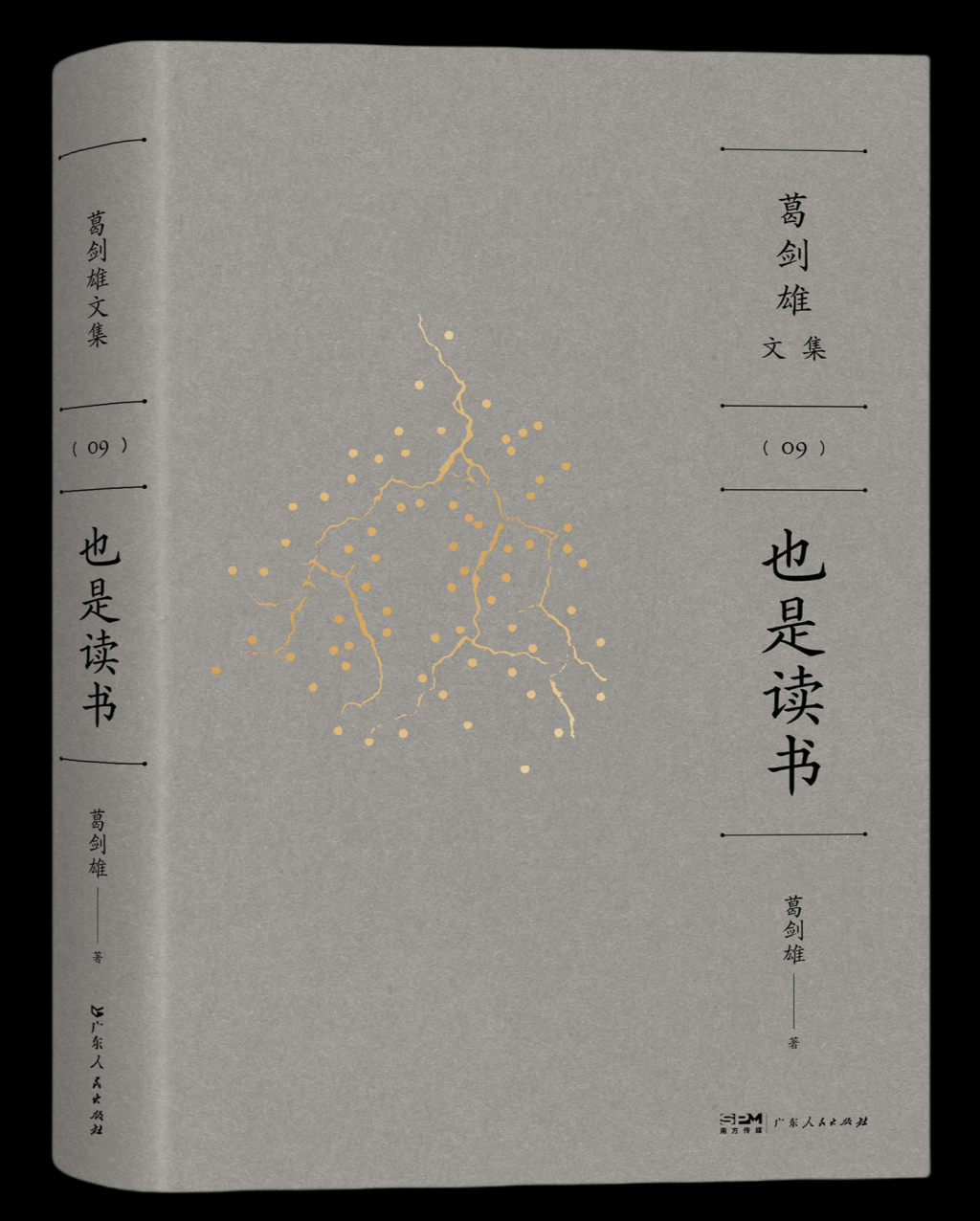
(本文摘自《也是读书:葛剑雄文集第9卷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,2025年3月,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。)











有话要说...